随意散漫,不求深刻,但求新见,葆守独立思想,张扬自由个性,或可反映艺林之点滴。
黄永玉称曾在友人(雕塑家郑可)处见到徐悲鸿旅法时的一张名片,上面写着:
巴黎落拓画家 徐悲鸿
陈传席客居融斋,夜与任我行谈刘海粟轶闻,彼手舞足蹈:“刘海票
任我行作客刘二刚午梦斋,适朱新建来访,朱尝与任我行称,如果出版放开,我要办刊物,就办一本《色情漫画》,这“色情”和“肉欲”本是分开的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周作人、胡适、林语堂、刘半农这些北大的名牌教授办了本《歌谣》杂志,第一期上登了三条征稿声明。第一条:我们征集各种民谣,不包括猥亵、淫秽的;第二期变成了“包括……”;第三期变成“尤欢迎……”为什么?因为他们从来稿中发现,最好的、最生动的、最有意思的便是这些带色的。记得一则刘半农整理的民谣,很有趣:“大姐走路俏俏的,两个奶子翘翘的;有心上前摸一把,心儿却是跳跳的。”朱随即兴画一图,并录之于其上。
《计算机世界》杂志的老板说,某年,一个东北黑龙江的订户一下子订了他们五万份,编辑部上上下下十分激动,一致要求我们领导亲自去一趟东北,与这位“知音”订户交流交流。待我们历尽千山万水到了那里,一看,原来是家小造纸厂,将《计算机世界》直接下厂打成纸浆,说这纸浆质量高。明知如此,还只能按订单照常供货,让他们去打“优质纸浆”。噢,强调一下:《计算机世界》杂志大八开,一百多页,定价四毛。
据友告知,韩羽先生是“恐迷”(恐:恐怖片也)。一般每晚能连看几碟,夜深而不知倦。老伴常嗔怒不休,却拿他没法。某夜,老伴独自无聊,壮胆凑来想看看究竟,未料吓出一身冷汗,遂致数夜不能安睡。后凡与人谈及此事,仍觉心儿直跳,絮絮叨叨叫苦不迭。……韩先生来京访友,客居友人处,竟日闭门,蹲在屋里独自放着VCD,夜愈深精神愈振;几天过去,已将友人家藏的碟片,扫了个通关。
3月8日,方向来访,说:现在那些要画的人真是可怕,名堂很多,防不胜防,我叔叔(方楚雄)就领教过一次。某日,来了一个“换画”的,带着一张豹皮。我叔叔虽然画动物,喜欢动物,但觉得家里放一张豹皮总不好,太煞风景。那人见我叔叔不想要,便说:方先生不喜欢,豹皮就暂留在您这儿,我要到乡下去,过几天来取。那人走后,我叔叔心里老犯嘀咕,豹子是国家保护动物,这家伙说不定就是个偷猎者呢。天天盼着他来取走。过了很久,来了一个人自称是某某的同乡,要将豹皮拿走。我叔叔心想,早该拿走,总算了却一桩心事。又过几天,留豹皮的那个人来了,说要取豹皮。叔叔说豹皮让你朋友取走了,叫某某。来人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:哎呀,哪是我的朋友嘛!是个骗子啊!竟嚎啕大哭起来。最后,我叔叔只得给他画一张四尺的豹子才将此事摆平。
这事还没完。过几天,汕头老家有人打电话给我叔,说买到一张他刚画的豹子,画贩子说是用豹皮和你换来的,不知真假。我叔叔便说了前几天的事。那人便放心买下,过些日,那人仍不放心,将“豹子”带来让我叔叔看看,果然,竟是张假的。原来那家伙拿到画后,马上找人仿了几张,倒到汕头的就是其中之一。真家伙还在他手里,不知他“克隆”出多少只豹子。
黄永玉说:某年,苗子、郁风从澳洲回来,广游名山大川,每到一地,俩人胃纳大开,专吃美味,某日,又吐又泻,我戏作一联送给他们:
重游旧南北
专呕好东西
8月8日画家周边说,我在黄山的时候,云谷山庄(酒店)老总跟我说:海老十上黄山,住在云谷。海老坐在滑杆(竹轿)上,一颠一颠的,远远看见山庄上的招牌,突然叫停下,用拐杖指前方,大声道:“谁写的?”老总说:“也是一位大师,吴作人大师写的。”刘大师梗着脖子正色道:“他算什么大师,他哪会写字。赶紧拿下来。”老总唯唯诺诺:“拿下来怎么办?”“刘大师写呗,我给你们写。”老总说:“我马上叫人取下来。”“取下来不行,砸掉,我来写!”
再后来刘大师走了,他们又把吴的牌挂了上去。山里人实在。老总说:不能不讲情谊,吴作人毕竟也是人物。
8月12日北京李燕打来电话:我曾经在政协会上说过,“双百”是否要改一下,百家争鸣肯定要打架,改成“百家自鸣”多好;百花齐放,怎么可能,牡丹开的时候,梅花谢了,应改为“百花第放”,有先有后,才能四季都有花。
曾有美术史家传任我行一心理秘诀:当你对自己的画信心低落的时候,不妨再去看看时人的作品,你对自己的画就会有信心了;当对自己的画沾沾自喜以为了不得的时候,就该去看看古人的东西了,它会让你张狂顿消的。边小燕以为未必,因为缺乏芝术感觉的人,恰恰是看见古人的东西就自我狂妄,看见时人的东西却生向慕之心。
10月24日《边缘・艺术》编辑部一行人专程到嘉兴访问吴藕汀老人。又偕藕公同访秀州书局。在“局长”范笑我写字桌的玻璃台板下,看到吴藕老自画像《瓦山野老意》的原迹复印件。瓦山野老者,实有其人,指吴履(1740-1801)。吴履有句名言叫“我看不得人,人亦看不得我”,故尝作《背立图》。吴藕汀老人也是“我看不得人,人亦看不得我”,故作此《瓦山野老意》。此图应《百美图》收集者包立民所作,可包立民却看不见吴画的深意,提出“可否在转身回眸点一下睛”。既“看不得人”,要“点睛”做啥?!
房宁在《读书》(2001年11期)杂志上发表《新的未必是好的》一文,摘录如下:
在学界,求新、求异更是蔚然成风。一个“新”可以把人捧上天,一句“没有新意”又足以贬得他无地自容。强调新的意义和价值,甚至以新为真,以新为美,就失之偏颇了,可谓“过犹不及”。
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: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,是二十世纪的劫难。他认为那些“对于新奇无休无止的追求”只要“不停地革新、革新、再革新的观念,它们所掩藏的,是一种不屈不挠并且由来已久的企图:毁坏、推倒、嘲笑,并连根拔除一切伦理道德原则。没有上帝、没有真理,宇宙是一片混乱,一切都是相对的。”它们的本质是“对于一切内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根深蒂固的敌视”,于是,“否定一切和否定所有的理想被视为一种勇敢的举动”,“毁坏成了这种桀骜不驯的主张所尊奉的最高信念”。在索尔仁尼琴看来,“迷恋新奇”除了获得“迫不及待的革新者们不绝于耳的自我赞美”之外,没有“任何有实在价值的创造”。
思想理论的创新是严肃的,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,绝非主观上可以随意“发展”、“创新”的。多如牛毛的新理论、新见解,轻易的体系创造,除了表明社会的浮躁心理外,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。
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度过了一百年,难道还不应变得更成熟一些吗?
按:此文疑是对“五四”以来惟新为美、浮浅弱智的学风的大反省。也可谓对“新论”作了一定评。美术界“新风”尤盛,尤幼稚,以致有人大言不惭:“宁可不好但要新的。”“新”本来就是骗人的东西多,皇帝的新装,不也是“新”的嘛!
浮碧先生对欧阳中石的学生说:欧阳先生我喜欢。但是,每次见到他的书法我必掩眼而过,怕有损对他的美好印象。因为,他的奚派老生唱得太棒了!
7月5日,诗人芒克、车前子、《中国文物报》编辑某、苏州文物商店祝效平、《边缘・艺术》编辑二人等聚饮,席间有人说,曾请齐良迟鉴定齐白石的画,齐良迟说不管真假,先放六千的鉴定费,再看画,“真”六千,“不真”也六千。如果要题字的话还得另外加码。
按:不知这段子真实与否。其实六千鉴定费收得还嫌太少了,花六千元钱赌一把算什么呢?假如是真,那还了得?因此收六千鉴定费是吓不退那些附庸风雅、买画行贿者的。
某领导人视察某美院,见墙上挂有一草书轴,驻足观望时,旁边跟随着的一人,为献殷勤而念了一遍。哪知此举引此领导大为不悦。休息时,该领导将刚才那首草书写的诗,背诵了一遍。此意在证明他是懂的,有学问的。马屁拍到马腿上了。
同一故事另一版本:某人送一草书轴,又奴性地附了一张打字的释文。领导为此大为不快,这不明摆着在以为该领导不懂草书嘛。
近日见朋友求来黄苗子写的书斋匾额,不觉大开眼界,黄老的字确实比古人更有新意,新就新在,他写字是先用炭条画出字形结构,再用毛笔描摹出之,又再反复修改,很是认真。真该更名叫设计书法。
2月7日夜,梅墨生打来电话:对吴冠中“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”的发言,我觉得实在不妥。
你强调艺术的人文关怀也对,但艺术也需要那么宏大的包袱吗?齐白石与鲁迅,不是一类人,不可比。就像飞机和轮船,X光科和消化科,泥瓦匠和木工,不是一类,怎么能比个高低呢?吴先生这个人实在滑稽。我对他没什么看法。只觉得很奇怪,很多作家在拿齐白石开涮,美术界也有很多人在说齐白石的不是,我觉得不是滋味。
边白:其实可能不是比不比的问题,而是更需要什么的问题。正需要泥匠的时候,却来了十个木匠,用得着吗?而当今文化领域中又岂止十个木匠,成百上千呀,斧子不会砍,锯子不会拉,却扛着“美术官”的头衔到处走穴。
12月5日,打电话约陈丹青稿,陈说:发以前的画,啃老本,没什么意思;发后来的画,要被人骂。都在骂我腐朽,其实骂也没什么。我现在没什么激情。你们出个题目由我来写的想法倒可以。
骂人都不会骂,“腐朽”是表扬。
3月6日晚,浙江范笑我打来电话:现代文学馆派二员去上海找章克标,希望他将自己的手稿捐给文学馆。按他们条文,被征集的作家应该是作协会员,章却不是。于是去找上海作协,作协说,加入可以,但需有两个以上作协的会员作介绍人。
范说:章倒有两个作家朋友,很有名,一个叫鲁迅,一个叫林语堂。唉,这是个好主意。可转念一想,这两位也都不是作协会员。
5月8日孔戈野来访说:某年,香港一贵宴请程十发、韩天衡等,步入大厅,迎面墙上正挂着程的大幅巨作。韩脱口而出:这……程公赶忙一捏韩手,止住话题。一席无话。散宴后,韩问:您为何不让我说?那么假的东西?程说:人家请我们吃饭,开心;我们吃人家饭,也开心。何必扫兴?!韩想:江湖还是老的辣。
有人问钟馗王画家姜也:你画的钟馗不错,应该好卖的吧?画家说,不好卖!为什么?老板买了钟馗去送人,人家不喜欢,钟馗是捉鬼的,当官的不喜欢。听说,有几个当官的挂了我画的钟馗后,不长时间就出事情了。清官则是不怕的。贪官怕的就是钟馗,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有鬼。所以钟馗是不能乱挂的。有位女士挂了我的钟馗以后,烦人的骚扰电话就没有了。
在南通造访九十五岁老画家尤无曲。谈到对当代中青年画家作品的看法,老人说“薄”。问他二十世纪最佩服的画家是谁,答“陈师曾……黄宾虹”。问李可染画,答“做作”。问黄秋园,答“石涛的皮毛”。问陈子庄,答“小画还行”。
9月1日,参加北大资源美术学院开学典礼。会上,美协某领导讲话:我希望大家做一个好画家,什么是好画家?首先是为人民服务,人民不喜欢你的画,你就没有出路。你的画要人民来买。像吴冠中说的,要专家点头,群众拍手!
任我行说:现在社会并不缺少画家,而是太多了。北大曾经是新文化新思想的摇篮。我希望你们将来走上社会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人,我们缺少的是有独立思想的画家。什么叫有思想,比如刚才这位先生说的话,你们要想一想,吴冠中的画没一幅是人民“喜欢”得起的。人民也在为生存奋斗,人民看不懂吴冠中的画更买不起吴冠中的画。买吴冠中的画基本上是资本家、官僚、商人和华侨。哪个学校敢说是为了培养大画家,肯定是在搞“传销”。
某日,无言居士说:这是一个制造文化垃圾的时代,我们也不怕说我们是制造文化垃圾,而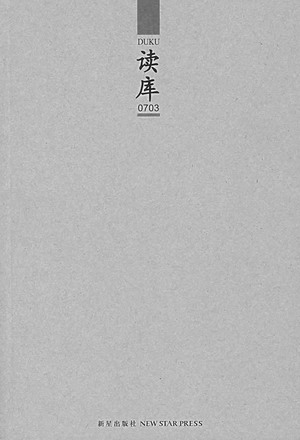 且我们要大量的造,如果你制造的垃圾太少,很快就会被历史清除,被其它垃圾覆盖。如果你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垃圾山,他们想清也清不掉,想盖也盖不了。那么,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垃圾画家,画史照样有你的位置存在。所以,如果你把文化垃圾堆积成一座泰山,照样可以成为神话,有很多人来朝拜你。
且我们要大量的造,如果你制造的垃圾太少,很快就会被历史清除,被其它垃圾覆盖。如果你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垃圾山,他们想清也清不掉,想盖也盖不了。那么,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垃圾画家,画史照样有你的位置存在。所以,如果你把文化垃圾堆积成一座泰山,照样可以成为神话,有很多人来朝拜你。
某拍卖行拍卖某画家作品,画家跑去指出作品是假,要求撤拍。拍卖行负责人却振振有词道:“作品的真假作者说了不算。”画家说:“那谁说了算?”负责人说:“要鉴定家说了算!因为你是当事人。”
两出版社编辑聚在一起,一位说:现在的画册是越俗越好卖,像“梅花王”、“猫王”、“虎王”之类我们社里是再三加印。另一位说:是啊,这些老干部们喜欢,我们社的编辑有水平的编的书不好卖,平庸的编辑编的反而很好卖,奖金也拿得多。
一次研讨会上,有人质疑崔某某、何某某等“大师”称谓,以为当代没有大师。一年轻人站出来说,我们就是要把他们二位捧成大师,为什么?如果我们把他们看成大师,那么,我们的参照是崔大师、何大师。如果现在没有大师,那么我们只能以黄宾虹、齐白石这些大师作参照,我们还有做大师的可能吗?
(摘自《读库0703》,新星出版社2007年7月版,定价:30.00元。原文标题《边缘人语》。)
